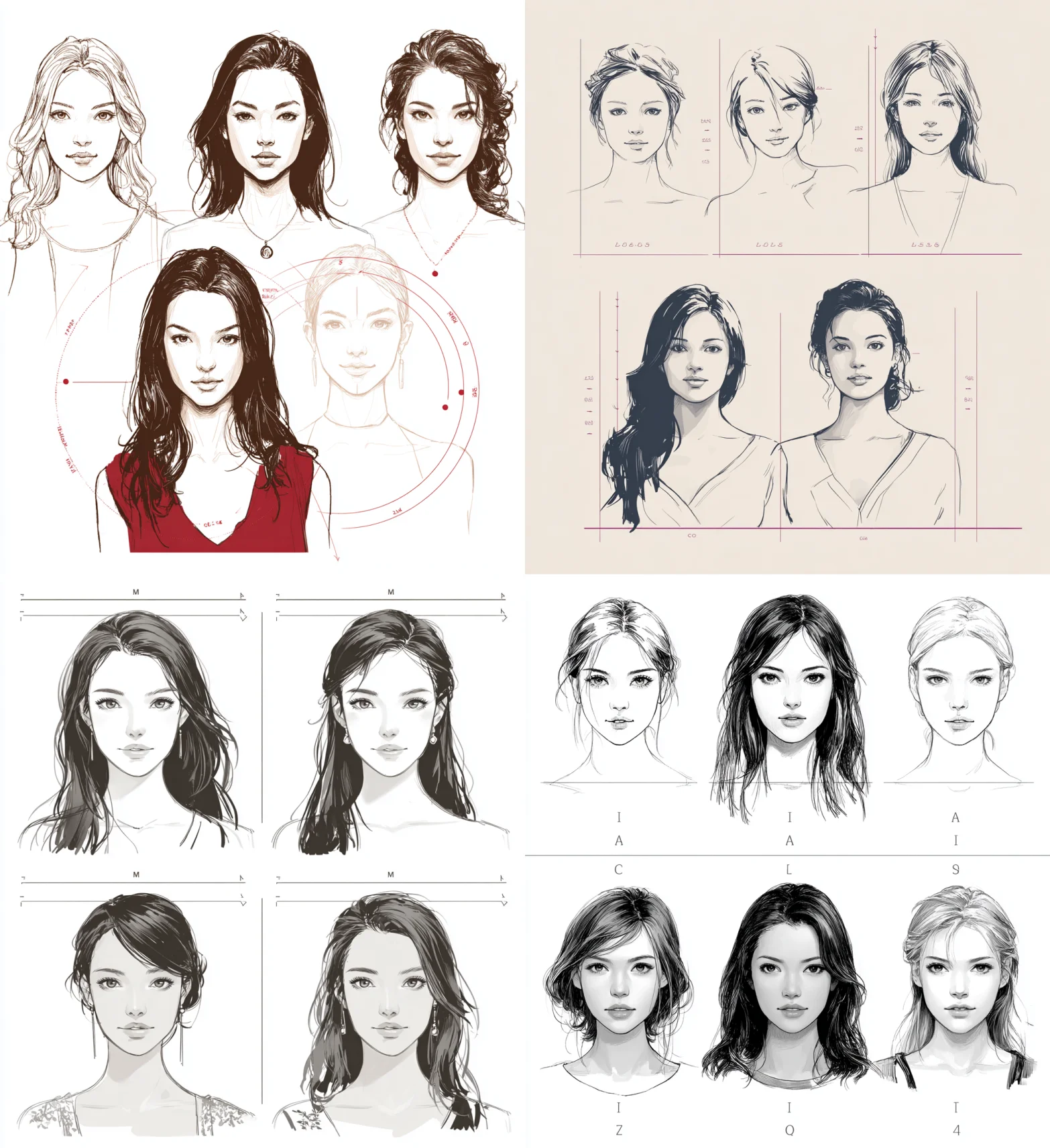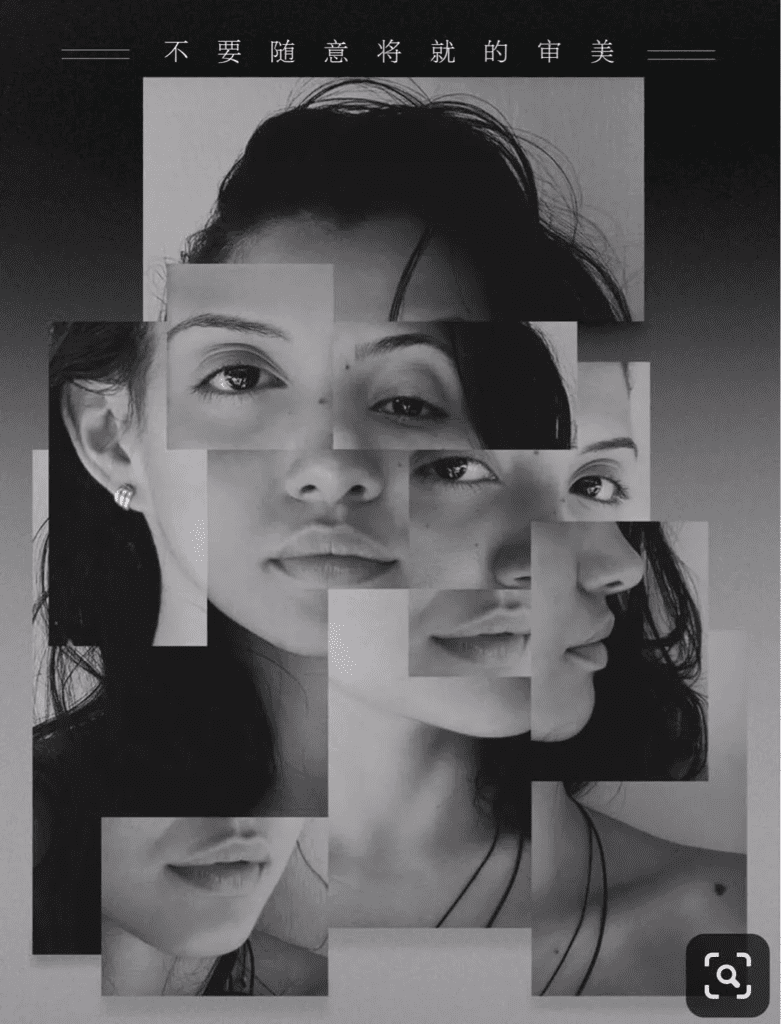为什么我对预制菜并不反对?

我认为它是我们未来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伴侣。虽然这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的话题,我还是想实话实说。
先讲三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我在大学化学实验室做实验时。我们有一瓶很脏的水,通过蒸馏法和一些类似气相色谱的分离过程,教授把处理后的水直接喝了。他说自己渴了。男生们还好,几个女生则惊呆了,心想老师怎么能喝这么脏的水?教授对我们说,水的化学结构就是 H₂O,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的水比你们见到的所有饮用水都要干净。这让我对科学的过程有了深刻的信任。
第二个场景是我在南开大学听一位院士的讲座。那时还不叫院士,叫中科院学部委员。他讲到了当时备受争议的杂交水稻,直言不讳地说,不要迷恋那些传下来的老种子。这些老种子不仅有病虫害,营养和质量也低,产量更是无法让我们吃饱。杂交水稻的产量不仅提升,还能抗倒伏、抗虫害等。这一切将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流,农业科技从传统的田间耕作,向种子的本质和能力延伸。而这一点对我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来说,影响巨大。袁隆平院士的事迹,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这正是科技改变生活的最好例证。
第三个场景是我自己的经历。过年的时候,我送给亲戚一块猪肉。我们老家杀了年猪,那是土猪,真的是在自家的山坡上养大的,基本没有饲料,猪自己找食。可这猪肉不够用,亲戚朋友们纷纷来拿,最后我自己也没剩多少。到了我回北京时,我带了一块猪肉给一个特别讲究美食的朋友。不巧,我带错了,正琢磨着怎么解释的时候,朋友打来电话说:「老于,这块肉真好吃,和市场上的不一样。」 我才发现我拿的是市场上买的饲料猪肉,而家里的土猪肉还在那儿放着。虽然我轻描淡写地告诉了她,但我觉得她的脸色并不太好。这让我意识到,人们对食材的固有认知和情感连接是多么的根深蒂固。

预制菜的话题引发了很多争议。我们所吃的东西,是否应该保持原汁原味的情结,深植于中国人的内心。这种情结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表现不一:老年人可能更关心口味是否正宗,是否符合他们记忆中的味道,以及购买和烹饪的便利性;而中年人则往往对传统烹饪方式和食材的本真味道更有执念,认为那才是 「家的味道」;年轻人则可能更关注食品的安全、营养,以及是否符合他们快节奏的生活方式。
随着我国社会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许多复杂的事情都被简化并制成标准化产品。这样,我们在日益精细的社会分工下,能够享受到更多、更新、更经济的产品和服务。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回到过去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事事都自己从头到尾手工制作,这在现代社会是否可行呢?我认为,像一些美食博主展示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和美食体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符号和审美表达,或许能满足一部分人的精神向往,但对绝大多数在城市中奔波的人们来说,并不现实。
我们常常会怀念过去,感叹 「小时候的味道」,但我们真的能抛弃现代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吗?预制菜也是如此。最近我也尝试购买了几份价格相对较高的预制菜,按照商家的推荐步骤进行烹饪,结果出乎意料,味道真的不错。无论是家常小炒、回锅肉、鱼香肉丝,还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东坡肉和小鸡炖蘑菇,都达到了可以接受甚至令人满意的水平。我还尝试了几种冷冻包子、蒸饺,也觉得很方便美味。虽然它们与手工现做的菜肴在口感和风味上可能存在细微差别,但对于忙碌的现代生活来说,已经完全足够。
现在,我的厨房也变得非常简单。以前常备的香菜、香葱、生姜、大蒜,我现在更多地选择脱水产品。这些脱水调料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而且在味道上也能满足基本需求。虽然新鲜蔬菜的口感确实更胜一筹,但在整体上,这些预制菜和半成品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那么未来会怎样呢?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逐渐适应并离不开的互联网和各种智能设备一样,会慢慢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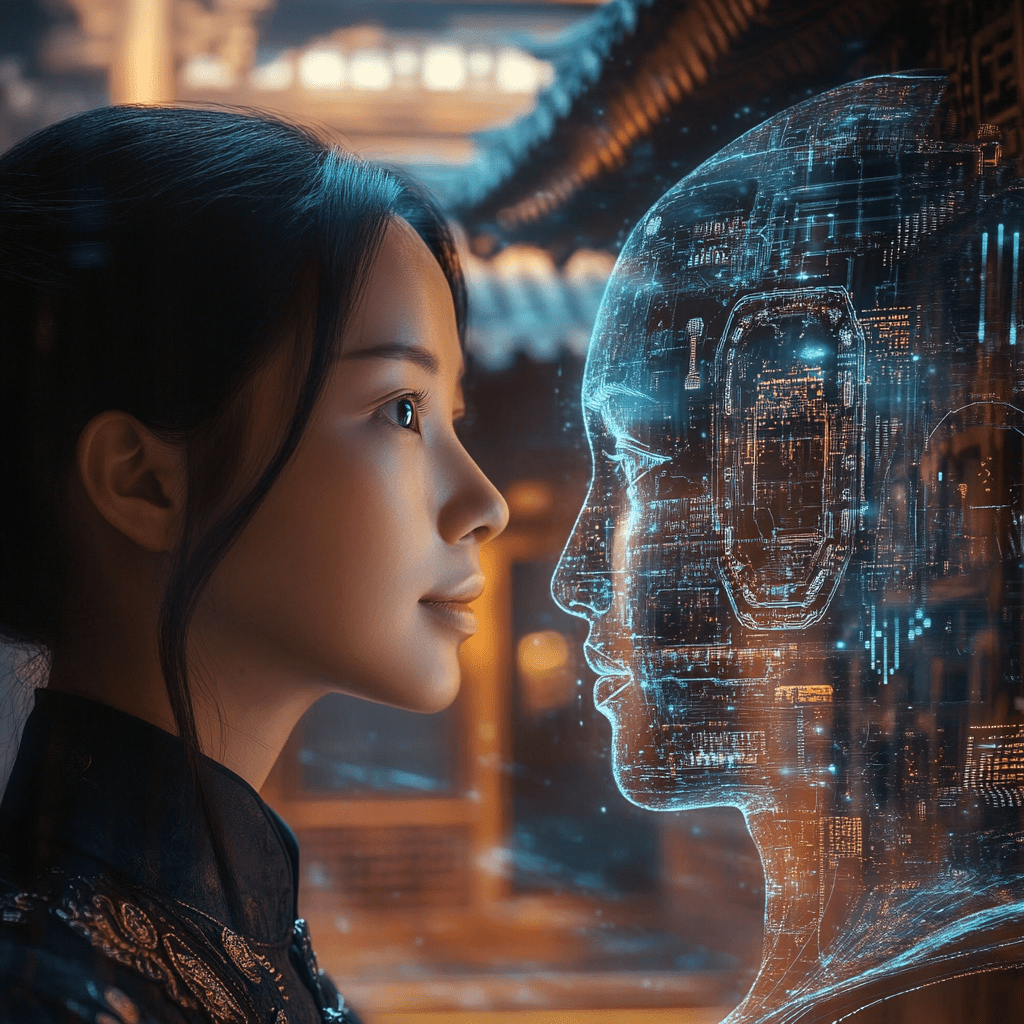
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品尝一份精心制作的预制菜时,我们不会再带有刻板印象,而是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家的味道、手工制作的温情,以及烹饪过程所带来的那份小小的成就感和家庭和睦的温馨氛围。即便仅仅从味蕾的满足和情绪价值的角度来看,预制菜也正在悄然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我们是否已经接受了这种更加便捷高效的饮食方式?我们又该如何将这种理念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在拥抱现代化的同时,也能传承对食物的尊重和热爱?这或许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